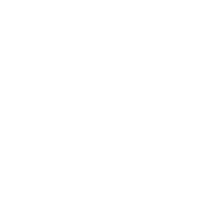程莉
人與人相識,大約是需要緣分的����。
如果喜歡或者景仰一個人——那種傾心的喜歡與景仰,既不必追星���,也不必性急����,就那么隱約地在心里牽掛著�����,也許他會在你生活的某一個路口�,等著和你邂逅,只要你和他有緣——我一向這樣認(rèn)為��。
于是有一天����,我認(rèn)識了季羨林老人��。
遙望季老�����,從讀他的散文開始。學(xué)術(shù)泰斗的博大精深����,我自無法領(lǐng)略,但我覺得����,他是一棵大樹,他散文中蘊涵著的平淡和悠遠(yuǎn)�,使人讀起來就像在樹下乘涼,就像和他聊天�����。
其實�,原可以早點走近他。前些年�,我從醫(yī)務(wù)部的報表中得知,他患白內(nèi)障住進(jìn)我們醫(yī)院��,想到大師近在咫尺,有一段期許等在那里��,忍不住慫恿辦公室主任:“咱們?nèi)タ纯醇纠习桑?rdquo;主任踟躕半日說:“恐怕探望他的人多����,就別打擾了。”
我只好作罷���,天天注意報表�����,直到他出院����。
后來認(rèn)識一位朋友———文化名人肖像攝影師魏德遠(yuǎn)���。小魏贈我一幅作品�,畫面是端坐書桌前的季老�����,肩上攀著一只白貓。有人評價它是一幅能在國際大賽上獲獎的佳作����。見我喜歡,小魏仗義地說:“季老和我很熟�����,如果你想認(rèn)識他��,我可以引見���。”“謝謝,不必了�。”我想,有珍藏照片的緣分����,足矣。
緣分可遇而不可求���。2000年初春的一天�,我的另一位朋友�����,作家周明突然來電話:“請你幫忙聯(lián)系一下季羨林教授看病的事好么?”原來季老又患眼疾����,人吃五谷雜糧總要生病的,幸而只是白內(nèi)障��。
一而再��、再而三����,我真的相信和季老有緣分在那里了。第二天不巧要外出�����,提前掛好著名白內(nèi)障專家施玉英教授的號��。周明一再叮嚀�����,季老高齡��,千萬別讓他久等。待我按時趕回�����,季老已先到����。雖然他的視力已經(jīng)很差,但一見我便頷首微笑�����,認(rèn)定是他要等的人���。陪同季老的李玉潔老師說:“昨天說要來看病,季老總惦記著�,一宿沒睡好,今兒一大早就起來了���。”
周明無意牽線�����,卻驗證了我的理論——相識不在刻意�,只要有緣。
眼前的大師與照片無異�,謙和、睿智���;更令我驚詫與感動的��,是他臉上浮現(xiàn)著孩童般的笑容���。
據(jù)說那天季老剛下車,就被醫(yī)院的門衛(wèi)邵師傅認(rèn)出——邵師傅正握著一冊《牛棚雜憶》讀得如癡如醉�,只見神往已久的大師突現(xiàn)眼前,大為驚喜��,舉著書就過來與季老握手��;季老顯然也頗感意外�,此乃又一段緣分。
住院手術(shù)����,施教授妙手回春,治療效果正如季老所言��,“大放光明”�。那日小魏探訪���,剛坐定,書法家歐陽中石也來了��,兩人握手��,原來認(rèn)識��。世界真是太小了����,隨處可能遇上熟人或者熟人的熟人——歐陽中石是我們老院長趙相印教授的校友,我對聞訊而來的趙院長說�,鬧了半天就我一個生人。
不見大師���,不知道什么是虛懷若谷��;未識季老,不知道什么叫學(xué)無止境�����。和他在一起�,就像和自己的長輩�����,用不著客套�,用不著拘束�,想到哪說到哪。
“您快九十歲了����,身體健康,頭腦又這么清楚��,有什么秘訣嗎�����?”我問���。
季老笑答:“我的長生之道是三不政策:不鍛煉���,不挑食,不嘀咕���。所謂不鍛煉��,是不刻意鍛煉��,但要多活動�����。”他穿著亦樸素�,一件半舊藏藍(lán)色中山裝便是“出門”禮服。他說:“去日本��,去臺灣�����,都穿它�����。家常衣服��,比這件就不如了����。”
一個沒有課的下午���,正上大學(xué)的女兒來到病房����,相差七十多歲年齡,現(xiàn)代女孩也和世紀(jì)老人有緣���。見到“小朋友”����,季老格外高興����,取出一本《留德十年》,不顧剛復(fù)明的眼睛還有些紅�,伏案提筆寫道:“熱愛祖國,孝順父母���,尊重師長��,同伴和睦�,珍視生命���,摯愛自然���,勤奮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,永不間斷———在病房中聊綴幾句�,與小友共勉���。”女兒捧書逐字念罷��,季老又細(xì)細(xì)解釋:“一個人��,心里首先要有祖國�����;孝敬長輩��,是中國人的傳統(tǒng)美德����;生命寶貴��,大自然美妙,要好好珍愛�����;希望你一輩子勤奮學(xué)習(xí)�����,不管是到了我這個年齡����,還是再大十歲�����,永遠(yuǎn)都不要間斷���。”女兒點頭��,突然摟住老人:“季爺爺�,我記住了����!”季老輕撫女兒肩頭,連聲說:“好孩子,好孩子�!”那情,那景���,讓我想起季老的名篇《三個小女孩》����。李老師感慨����,在一旁說,此番住院���,季老感想頗多�����,出院后肯定有好文章�����。
一晃又是幾年過去����,手撫季老親贈的四卷散文集,一邊期待這位耄耋老人的新作����,一邊想:與大師相識,乃三生有幸����。我以何德�,修得此緣在世間呢?